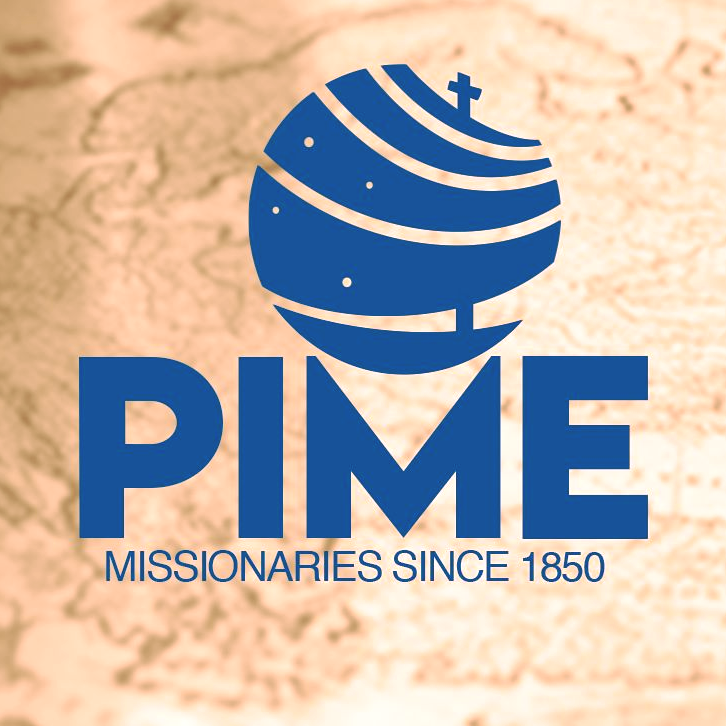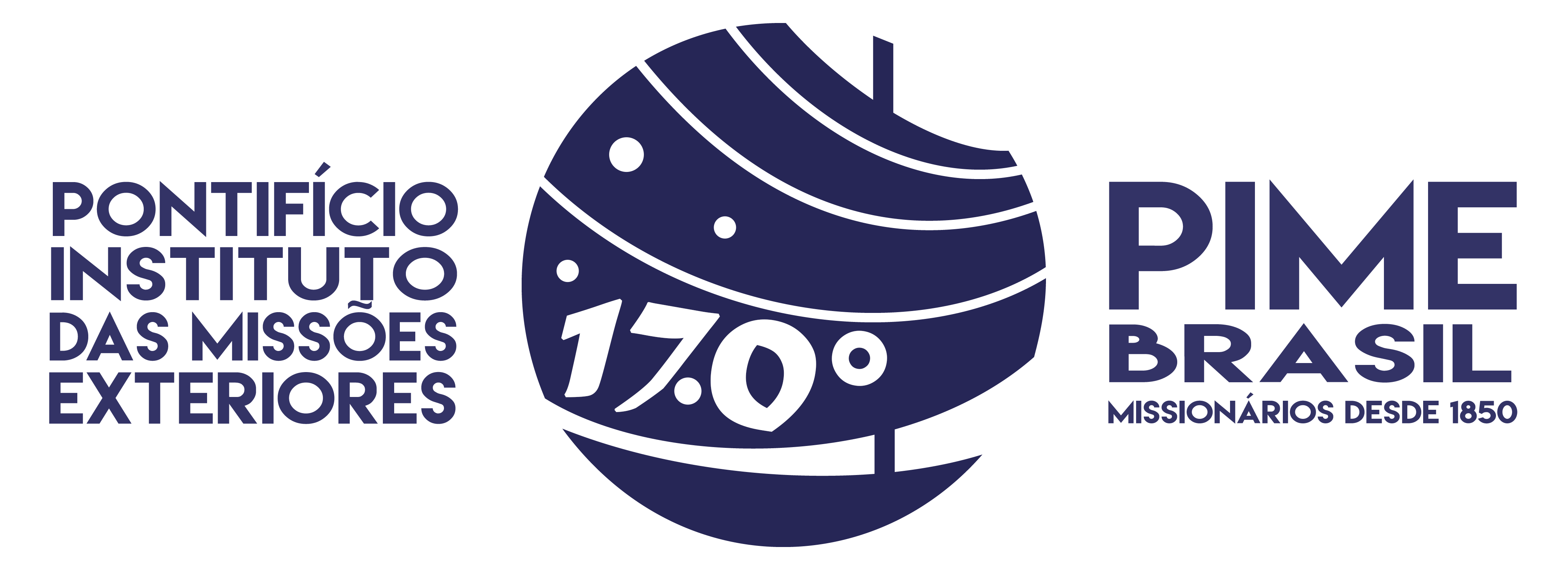дё»ж•ҷеӣўиҒ”еҗҲдјҡеҰӮдҪ•иө°еңЁдәҡжҙІи·ҜдёҠ
гҖҠдәҡжҙІж–°й—»гҖӢдё»д»»д»ҠеӨ©еңЁзҪ—马еҮәеёӯз”ұиӢҘжңӣ·дҝқзҰ„дәҢдё–е®—еә§зҘһеӯҰйҷўдё»еҠһзҡ„“еңЈзҘһзҹҘйҒ“иҰҒеёҰжҲ‘们еҺ»е“ӘйҮҢ”дјҡи®®ж—¶еҸ‘иЎЁи®ІиҜқгҖӮ “дёүйҮҚеҜ№иҜқ”жҢҮзҡ„жҳҜеҶ…еҝғзҡ„йҒ“и·ҜгҖҒеҜ№иҮӘз”ұе’ҢжӯЈд№үзҡ„жүҝиҜәгҖҒд»ҘеҸҠи®Іиҝ°иҖ¶зЁЈзҡ„ж•…дәӢпјҡжўөи’ӮеҶҲ第дәҢж¬ЎеӨ§е…¬дјҡи®®еңЁдёңж–№зҡ„жҺҘеҫ…йқўиІҢгҖӮ
зҪ—马пјҲдәҡжҙІж–°й—»пјү -“еңЈзҘһзҹҘйҒ“зҘӮе°ҶеёҰжҲ‘们еҺ»е“ӘйҮҢ”жҳҜдёҖж¬Ўд»Ҙ“и·Ёе®—ж•ҷдәәж–Үдё»д№ү”дёәдёӯеҝғзҡ„еӣҪйҷ…дјҡи®®зҡ„дё»йўҳпјҢиҜҘдјҡи®®зӣ®еүҚжӯЈдәҺ4жңҲ1ж—ҘиҮі2ж—ҘеңЁзҪ—马иӢҘжңӣ·дҝқзҰ„дәҢдё–пјҲJohn Paul IIпјүе®—еә§зҘһеӯҰйҷўдёҫиЎҢпјҢиҜҘдјҡи®®з”ұзү§иҒҢе®Әз« иҝҗеҠЁеҸ‘иө·пјҢз”ұзҘһеӯҰ家зҡ®е°”е®үжқ°жҙӣ·еЎһе…ӢйҮҢпјҲPierangelo Sequeriпјүдё»жҢҒгҖӮд»ҠеӨ©дёҠеҚҲпјҢгҖҠдәҡжҙІж–°й—»гҖӢдё»д»»жҹҜжҜ…йң–пјҲ Gianni CrivellerпјүзҘһзҲ¶д№ҹеңЁдјҡи®®дёҠеҸ‘иЁҖпјҢеҸ‘иЎЁдәҶйўҳдёә“жўөи’ӮеҶҲ第дәҢж¬ЎеӨ§е…¬дјҡи®®еңЁж¬§жҙІд»ҘеӨ–жҺҘеҸ—зҡ„еҠЁжҖҒе’Ңиҫ©иҜҒи§ҶйҮҺгҖӮдәҡжҙІзҡ„дҫӢеӯҗ”зҡ„жҠҘе‘ҠгҖӮдёӢйқўжҲ‘们еҸ‘иЎЁдәҶд»–зҡ„жј”и®Ізҡ„йғЁеҲҶж‘ҳеҪ•гҖӮ
1. и§Јж”ҫгҖҒж–ҮеҢ–йҖӮеә”дёҺеҜ№иҜқ
жўөи’ӮеҶҲ第дәҢж¬ЎеӨ§е…¬дјҡи®®еҸ‘иЎЁеҗҺдәҢеҚҒе№ҙйҮҢеңЁйқһ欧жҙІиғҢжҷҜдёӢзҡ„жҺҘеҸ—еҺҶеҸІеҸҜд»Ҙз”ЁеӣӣдёӘеӯ—жқҘжҸҸиҝ°пјҡи§Јж”ҫгҖҒж–ҮеҢ–йҖӮеә”гҖҒеҜ№иҜқе’Ңдё–дҝ—еҢ–гҖӮдәә们еҖҫеҗ‘дәҺе°Ҷиҝҷдәӣдё»йўҳдёҺеӣӣдёӘйўҶеҹҹиҒ”зі»иө·жқҘпјҡдёӯзҫҺжҙІе’ҢеҚ—зҫҺжҙІзҡ„и§Јж”ҫгҖҒйқһжҙІзҡ„ж–ҮеҢ–йҖӮеә”гҖҒдәҡжҙІзҡ„еҜ№иҜқд»ҘеҸҠ欧жҙІе’ҢеҢ—зҫҺжҙІзҡ„дё–дҝ—еҢ–гҖӮ
дёҠиҝ°жҸҗеҮәзҡ„ж–№жЎҲ并жңӘе……еҲҶеҸҚжҳ еҮәеҪ“ең°жғ…еҶөе’ҢжҢ‘жҲҳзҡ„еӨҚжқӮжҖ§пјҡи§Јж”ҫгҖҒж–ҮеҢ–йҖӮеә”е’ҢеҜ№иҜқе·Іи§ҰеҸҠеҗ„еӨ§жҙІгҖӮеҗҢж ·зҡ„жғ…еҶөд№ҹеҸ‘з”ҹеңЁдёҺеҗҺзҺ°д»ЈжҖ§е’ҢеҗҺдәәж–Үдё»д№үзҡ„з»“жһңзӣёе…ізҡ„жҷ®йҒҚеӯҳеңЁзҡ„зҺ°иұЎпјҢеҚідё–дҝ—еҢ–гҖӮ
иҝҷдёӘж–№жЎҲеҝҪз•ҘдәҶеӨ§жҙӢжҙІпјҢеҘҪеғҸжҫіжҙІе’ҢзәҪиҘҝе…°еңЁжҹҗдәӣж–№йқўеҸҜд»Ҙиў«и§ҶдёәиҘҝж–№дё–з•Ң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иҖҢе№ҝйҳ”зҡ„е·ҙеёғдәҡзәҪеҮ еҶ…дәҡе’ҢиҜҘең°еҢәзҡ„е…¶д»–еІӣеұҝеҲҷжҳҜиҮӘжҲҗдёҖдҪ“гҖҒе…·жңүзү№ж®Ҡзү№еҫҒзҡ„дё–з•ҢгҖӮ
2. дәҡжҙІдё»ж•ҷеӣўиҒ”еҗҲдјҡзҡ„дёүйҮҚеҜ№иҜқ
е…ідәҺдәҡжҙІеҜ№жўөи’ӮеҶҲдё»ж•ҷеӣўеӨ§дјҡзҡ„жҺҘеҫ…пјҢйҰ–е…ҲеҖјеҫ—жіЁж„Ҹзҡ„жҳҜдәҡжҙІдё»ж•ҷ们йҖҸиҝҮдәҡжҙІдё»ж•ҷеӣўиҒ”еҗҲдјҡпјҲFABCпјүе…ұеҗҢеҠӘеҠӣжүҖд»ҳеҮәзҡ„е·ЁеӨ§еҠӘеҠӣгҖӮиҜҘиҒ”еҗҲдјҡжҲҗз«ӢдәҺ1970е№ҙпјҢжұҮйӣҶдәҶеӨ§зәҰ20дёӘдё»ж•ҷеӣўпјҢ并еҲ¶е®ҡдәҶдёҖзі»еҲ—д»ӨдәәеҚ°иұЎж·ұеҲ»зҡ„жҢҮеҜјж–№й’ҲгҖҒж–Ү件е’ҢеҖЎи®®пјҢдёәжўөи’ӮеҶҲ第дәҢж¬Ўдјҡи®®еңЁдәҡжҙІзҡ„жҺҘеҸ—дә§з”ҹдәҶзңҹжӯЈзҡ„з§ҜжһҒеҪұе“ҚгҖӮдәҡжҙІеҹәзқЈж•ҷдјҡиҒ”еҗҲдјҡзҡ„йҒ“и·ҜжҳҜеј•еҜјдәҡжҙІж•ҷдјҡж‘Ҷи„ұж®–ж°‘дҪҝе‘ҪпјҢйҖҸиҝҮеҗҺж®–ж°‘жү№еҲӨпјҢиө°еҗ‘дәҡжҙІи®ӨеҗҢгҖӮ
жңҖиғҪд»ЈиЎЁдәҡжҙІеҹәзқЈж•ҷеҚҸдјҡеҸ–еҗ‘зҡ„ж–№жЎҲжҳҜ“дёүйҮҚеҜ№иҜқ”пјҡдёҺдәҡжҙІе®—ж•ҷдј з»ҹзҡ„еҜ№иҜқгҖҒдёҺеҸӨд»Јж–ҮеҢ–зҡ„еҜ№иҜқгҖҒд»ҘеҸҠдёҺз©·дәәзҡ„еҜ№иҜқгҖӮжҲ‘们еҸ‘зҺ°иҝҷйҮҢжңүдёүеӨ§жҢ‘жҲҳпјҡдёҺдёҚеҗҢдҝЎд»°зҡ„дҝЎеҫ’еҜ№иҜқгҖҒж–ҮеҢ–йҖӮеә”гҖҒд»ҘеҸҠдёәз©·дәәжҸҗдҫӣж‘Ҷи„ұеҺӢиҝ«е’Ңиҙ«з©·зҡ„йҖүжӢ©гҖӮ
еҖҹжӯӨжңәдјҡпјҢжҲ‘жғіеҗ‘еңЁ2024е№ҙ12жңҲ2ж—ҘеҺ»дё–зҡ„马еҝғж…§еҘіеЈ«пјҲCora MateoпјүиҮҙ敬пјҢеҘ№еҗ‘жҲ‘д»Ӣз»ҚдәҶFABCзҡ„еҚ“и¶Ҡе·ҘдҪңгҖӮеҘ№жқҘиҮӘиҸІеҫӢе®ҫпјҢеҗҺжқҘдҪҸеңЁеҸ°ж№ҫпјҢеңЁеҸ°ж№ҫзҡ„иҸІеҫӢе®ҫеӨ©дё»ж•ҷдјҡе·ҘдҪңдәҶ25е№ҙпјҢ并еҸ‘жҢҘдәҶйҮҚиҰҒдҪңз”ЁпјҡеҘ№жҳҜ第дёҖдҪҚеҮәд»»з§ҳд№Ұй•ҝзҡ„е№ідҝЎеҫ’еҘіжҖ§гҖӮеҮӯеҖҹе…¶еқҡејәзҡ„дёӘжҖ§е’Ңйӯ…еҠӣпјҢеҘ№еңЁжҺЁеҠЁдәҡжҙІж•ҷдјҡдёӯзҡ„е№ідҝЎеҫ’гҖҒе№ҙиҪ»дәәе’ҢеҰҮеҘіеҸ‘еұ•ж–№йқўеҸ‘жҢҘдәҶйҮҚиҰҒдҪңз”ЁгҖӮ
3. еҶ…еңЁд№ӢйҒ“
1990е№ҙд»ЈеҲқжңҹпјҢжҲ‘еңЁеҸ°ж№ҫжңүе№ёз»“иҜҶдәҶиҖ¶зЁЈдјҡдј ж•ҷеЈ«гҖҒжІүжҖқеӨ§еёҲдјҠеӨ«·жӢүеҸӨжҒ©пјҲYves RaguinпјүгҖӮеҪ“ж—¶жҲ‘еңЁеҸ°еҢ—з•ҷеӯҰпјҢд»–еҪұе“ҚдәҶжҲ‘зҡ„еӯҰдёҡе’Ңдј ж•ҷеҖҫеҗ‘гҖӮжӢүйҮ‘жҸҗеҮәеҶ…еңЁжҖ§е’ҢзІҫзҘһеҜ№иҜқзҡ„йҒ“и·ҜжҳҜиҝһз»“дёңж–№е®—ж•ҷе’Ңж·ұеҲ»зҡ„еҹәзқЈж•ҷзҘһз§ҳдј з»ҹзҡ„иҒ”зі»гҖӮ
д»–е°Ҷеӯ”еӯҗгҖҒеӯҹеӯҗгҖҒиҖҒеӯҗе’Ңеә„еӯҗзӯүдёӯеӣҪеӨ§еёҲпјҢдҪӣж•ҷе’ҢеҚ°еәҰж•ҷзҡ„еңЈе…ёдҪңиҖ…дёҺеЎ”е°”иӢҸж–Ҝзҡ„дҝқзҰ„пјҲPaul of TarsusпјүгҖҒдәҡз•Ҙе·ҙеҸӨзҡ„зӢ„еҘҘе°јдҝ®ж–ҜпјҲDionysius the AreopagiteпјүгҖҒиүҫе…Ӣе“Ҳзү№еӨ§еёҲе’Ңе…¶д»–дёӯдё–зәӘеҹәзқЈе®—ж•ҷзҘһз§ҳдё»д№үиҖ…иҒ”зі»иө·жқҘпјҢ然еҗҺдёҺеҚҒеӯ—иӢҘжңӣпјҲJohn of the Crossпјүе’Ңйҳҝз»ҙжӢүзҡ„еҫ·иӮӢж’’пјҲTeresa of AvilaпјүиҒ”зі»иө·жқҘгҖӮ
еңЁдёҠжө·е’ҢеҸ°еҢ—з”ҹжҙ»еӨҡе№ҙеҗҺпјҢжӢүеҸӨжҒ©дәҺ1968е№ҙиҝ”еӣһе·ҙй»ҺпјҢеҗ¬еҲ°е№ҙиҪ»дәәеңЁиЎ—дёҠй«ҳе–Ҡ“еӨ©дё»е·Іжӯ»”гҖӮд»–еҜ№жӯӨж„ҹеҲ°йңҮжғҠпјҢ并ж„ҸиҜҶеҲ°еҗҺеҹәзқЈе®—ж•ҷ欧жҙІзҡ„еҗҺе®—ж•ҷз»“жһңпјҲд»–жІЎжңүдҪҝз”ЁиҝҷдәӣжңҜиҜӯпјүгҖӮд»–зңӢеҲ°дәҶеҹәзқЈе®—ж•ҷдёҺдёңж–№зҡ„жҺҘи§Ұдёә欧жҙІе№ҙиҪ»дәәзҡ„зІҫзҘһд№Ӣж—…д»ҘеҸҠдәҡжҙІзҡ„зҰҸйҹідј ж•ҷдәӢдёҡжң¬иә«еёҰжқҘзҡ„ж–°жңәдјҡгҖӮдёҺдёңж–№е®—ж•ҷзҡ„жҺҘи§ҰеҸҜд»Ҙи®©жҲ‘们йҮҚж–°и®ӨиҜҶеҹәзқЈж•ҷдҝЎжҒҜзҡ„зІҫзҘһеұӮйқўпјҢиҖҢиҝҷдёҖеұӮйқўжӣҫеӣ еҹәзқЈе®—ж•ҷеҜ№ж•ҷд№үеұӮйқўзҡ„ејәи°ғиҖҢиў«иҫ№зјҳеҢ–гҖӮ
е…¶д»–з»ҸеҺҶиҝҮиҝҷж¬ЎеӨ§е…¬дјҡи®®е’ҢеӨ§е…¬дјҡи®®еҗҺзҡ„зІҫзҘһеҜјеёҲд№ҹиҜҒе®һдәҶиҝҷз§ҚзӣёйҒҮзҡ„еҸҜиғҪжҖ§пјҡжңұе°”ж–Ҝ·и’ҷжІҷе®ҒпјҲJules MonchaninпјүзҘһзҲ¶гҖҒжң¬з¬ғдјҡдҝ®еЈ«дәЁеҲ©·еӢ’зҙўе…Ӣж–ҜпјҲHenri Le SauxпјүгҖҒдҝ®еЈ«жҜ”еҫ··ж јйҮҢиҸІж–ҜпјҲBede GriffithsпјүгҖҒиҘҝеӨҡдјҡдҝ®еЈ«еј—жң—иҘҝж–Ҝ·й©¬дҝ®пјҲFrancis MahieuпјүгҖҒеҚ°еәҰиЈ”иҘҝзҸӯзүҷзҘһеӯҰ家йӣ·и’ҷ·жҪҳе°јеҚЎпјҲRaimon PanikkarпјүпјҢ他们йғҪеңЁеҚ°еәҰе·ҘдҪңгҖӮзү№жӢүжҷ®жҙҫдҪң家жүҳ马ж–Ҝ·й»ҳйЎҝпјҲThomas MertonпјүеҜ№дёҺжі°еӣҪдҪӣж•ҷзҡ„еҜ№иҜқдә§з”ҹдәҶжө“еҺҡзҡ„е…ҙи¶ЈпјҢиҖ¶зЁЈдјҡеЈ«йӣЁжһң·жӢүиҗЁеӢ’пјҲHugo LasalleпјүеҲҷеҜ№ж—Ҙжң¬зҰ…е®—дҪӣж•ҷдә§з”ҹдәҶжө“еҺҡзҡ„е…ҙи¶ЈгҖӮ
4. дёҺж–ҮеҢ–дј з»ҹзҡ„еҜ№иҜқ
иҖҢеңЁдёӯеӣҪпјҢз”ұдәҺж”ҝжІ»иҝҗеҠЁпјҢеӨ©дё»ж•ҷеӣўдҪ“зӣҙеҲ°дәҢеҚҒдё–зәӘе…«еҚҒе№ҙд»ЈжүҚжҒўеӨҚдәҶжңҖдҪҺйҷҗеәҰзҡ„е…¬е…ұз”ҹжҙ»гҖӮеҸ°ж№ҫиҷҪ然дёҚе®һиЎҢиҮӘз”ұеҸҠж”ҝжІ»еӨҡе…ғеҢ–пјҢдҪҶж—©еңЁ1970е№ҙд»Јдҫҝе·ІејҖе§Ӣе°қиҜ•ж–ҮеҢ–иһҚеҗҲгҖӮдҫӢеҰӮпјҢжҲ‘еңЁй«ҳйӣ„пјҲжҲ‘ејҖе§Ӣдј ж•ҷз”ҹж¶Ҝзҡ„еҹҺеёӮпјүе°ұжӣҫз»Ҹиҝҷж ·еҒҡиҝҮгҖӮиҝҷйҮҢзҡ„ж•ҷе ӮеңЁе»әзӯ‘дёҠйҮҮз”ЁдәҶдёӯеӣҪеҜәеәҷзҡ„йЈҺж јпјҢе…¶дёӯи®ҫжңүжҢүз…§дёӯеӣҪзӨјд»ӘдҫӣеҘүзҘ–е…ҲзүҢдҪҚзҡ„зҘӯеқӣгҖӮеҗҺиҖ…жһҒеӨ§ең°еҪұе“ҚдәҶеңЁдёӯеӣҪзҡ„дј ж•ҷжҙ»еҠЁпјҢдҪҶеңЁ1939е№ҙеҫ—еҲ°дәҶи§ЈеҶігҖӮжңүдәӣзҹӣзӣҫзҡ„жҳҜпјҢиҝҷеә§дҫӣеҘүй”ЎиҖ¶зәіеңЈеҠ еӨ§еҲ©иӮӢпјҲSt Catherineпјүзҡ„ж•ҷе ӮеұһдәҺйҒ“жҳҺдјҡпјҢиҖҢ他们еҪ“ж—¶жҳҜиҝҷдәӣд»ӘејҸзҡ„йӘ„еӮІеҸҚеҜ№иҖ…гҖӮ
еҸ°ж№ҫиҫ…д»ҒеӨ§еӯҰи®ҫжңүз”ЁдәҺиҝӣиЎҢзӨјд»Әе®һйӘҢзҡ„жҲҝй—ҙпјҢ并жң—иҜ»дёӯеӣҪеҸӨе…ёз»Ҹж–ҮгҖӮиҝҷдёӘжғіжі•жҳҜдёәдәҶи®ӨзңҹеҜ№еҫ…е…ідәҺеңЈиЁҖзҡ„з§Қеӯҗе’Ңе®—ж•ҷдј з»ҹдёӯйҡҗи—Ҹзҡ„иҙўеҜҢзҡ„и°ғи§Је»әи®®пјҢзҺ°ж—¶иҝҷдәӣдёҙж—¶е°қиҜ•е·ІдёҚеҶҚжңүж•ҲгҖӮ
5. дәҡжҙІзҡ„иҙ«з©·дёҺе®—ж•ҷдҝЎд»°еҸҠдәҡжҙІи§Јж”ҫзҘһеӯҰ
и¶ҠеҚ—зҘһеӯҰ家дјҜеӨҡзҰ„·жҪҳпјҲPeter PhanпјүиҜҙпјҢеҜ№дәҺжўөи’ӮеҶҲ第дәҢж¬ЎеӨ§е…¬дјҡи®®еҗҺзҡ„еҚҒе№ҙдёӯеңЁзҪ—马宗еә§еӨ§еӯҰеӯҰд№ зҡ„и®ёеӨҡдәҡжҙІзҘһеӯҰ家жқҘиҜҙпјҢиҖ¶зЁЈдјҡзҘһеӯҰ家йҳҝжҙӣдјҠдҝ®ж–Ҝ·зҡ®е°”ж–ҜпјҲAloysius PierisпјҢеҺҹзұҚж–ҜйҮҢе…°еҚЎ) зҡ„жҖқжғі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еңЁгҖҠдәҡжҙІи§Јж”ҫзҘһеӯҰгҖӢ(1986 е№ҙ) дёӯиЎЁиҫҫжҖқжғізӮёеј№пјҢе°ұеғҸдёҖйў—“иЎЁиҫҫжҖқжғізҡ„жҖқжғізӮёеј№”гҖӮ “1972 е№ҙеӣһеҲ°еҚ—и¶ҠеҗҺпјҢжҲ‘е®ҢжҲҗдәҶеӯҰеЈ«еӯҰдҪҚзҡ„еӯҰд№ пјҢжҲ‘з—ӣиӢҰең°ж„ҸиҜҶеҲ°пјҢжҲ‘еңЁзҪ—马еӯҰеҲ°зҡ„зҘһеӯҰзҹҘиҜҶж №жң¬жІЎз”ЁпјҢ”д»–иҜҙгҖӮ
зҡ®е°”ж–ҜжҳҜиҮізӣ®еүҚдёәжӯўдәҡжҙІжңҖе…·еҪұе“ҚеҠӣзҡ„зҘһеӯҰ家д№ӢдёҖпјҢд»–и®Өдёәи§Јж”ҫеҝ…йЎ»жҲҗдёәдәҡжҙІеӨ§йҷҶзҘһеӯҰзҡ„зӣ®ж ҮпјҡеҜҢдәәеҝ…йЎ»ж‘Ҷи„ұ他们зҡ„иҙўеҜҢпјҲжІЎжңүиҙўеҜҢе°ұдёҚеҸҜиғҪиҝӣе…ҘеӨ©еӣҪпјүпјҢз©·дәәеҝ…йЎ»ж‘Ҷи„ұиў«иҝ«зҡ„иҙ«еӣ°гҖӮ
еҜ№зҡ®е°”ж–ҜжқҘиҜҙпјҢдәҡжҙІиғҢжҷҜеҶіе®ҡдәҶдәҡжҙІеӨ§йҷҶзҡ„зҘһеӯҰж–№жі•е’Ңй—®йўҳгҖӮзӨҫдјҡиғҢжҷҜжҳҜзі»з»ҹжҖ§зҡ„иҙ«еӣ°пјҢе®—ж•ҷиғҢжҷҜжҳҜе®—ж•ҷеӨҡе…ғеҢ–пјҢж—ўжҳҜ“е®Үе®ҷзҡ„”е®—ж•ҷпјҢд№ҹжҳҜдәәж°‘е’Ңз»„з»Үзҡ„е®—ж•ҷгҖӮ
дәҡжҙІзҡ„е®—ж•ҷжҖ§е’Ңиҙ«еӣ°жҖ§зҡ„еҸҢйҮҚзү№жҖ§еҜјиҮҙдәҶдәҡжҙІеҹәзқЈе®—ж•ҷзҡ„“еҸҢйҮҚжҙ—зӨј”пјҢеҚі“дәҡжҙІиҙ«еӣ°жҖ§зҡ„иҖ¶зЁЈеҸ—йҡҫең°”е’Ң“дәҡжҙІе®—ж•ҷжҖ§зҡ„зәҰж—ҰжІі”гҖӮиҝҷеҸҢйҮҚжҙ—зӨјжһ„жҲҗдәҶжӢҝж’’еӢ’зҡ„иҖ¶зЁЈжүҖжҸҗдҫӣзҡ„“еҺҹе§Ӣи§Јж”ҫз»ҸйӘҢ”гҖӮжҙ—зӨјжҳҜеңЁиҙ«з©·зҡ„еҠ з•ҘеұұдёҠиҝӣиЎҢзҡ„пјҢеҸҜд»ҘйҖүжӢ©жҲҗдёәз©·дәәжҲ–дёәз©·дәәжңҚеҠЎгҖӮзәҰж—Ұзҡ„е®—ж•ҷжҙ—зӨјиҰҒжұӮдәҡжҙІзҡ„зҘһеӯҰз ”з©¶еҝ…йЎ»дёҺе…¶д»–е®—ж•ҷзҡ„дҝЎеҫ’еҗҲдҪңдёҺеҜ№иҜқгҖӮ
6. ж•ҷдјҡеҸҠе…¶йўҶиў–еҜ№иҮӘз”ұе’ҢжӯЈд№үзҡ„жүҝиҜә
дәҡжҙІзҡ„ж•ҷдјҡзЎ®е®һз»ҸеҺҶдәҶдёәж°‘ж—ҸзӨҫдјҡи°ӢзҰҸеҲ©зҡ„зӨҫдјҡи§Јж”ҫгҖӮдёҖдәӣеӨ©дё»ж•ҷйўҶиў–еңЁдәүеҸ–дәәж°‘иҮӘз”ұе’Ңж°‘дё»зҡ„ж–—дәүдёӯеҸ‘жҢҘдәҶе…ҲзҹҘжҖ§е’Ңи¶…еҮЎйӯ…еҠӣзҡ„дҪңз”Ёпјҡ马尼жӢүзҡ„иҫӣжө·з»өпјҲJaime SinпјүжһўжңәпјҲд»–еҸ‘иө·дәҶзҺ«з‘°з»Ҹйқ©е‘ҪпјҢз»“жқҹдәҶ1986е№ҙ马科ж–ҜпјҢMarcosпјҢзӢ¬иЈҒз»ҹжІ»пјүпјӣйҮ‘еҜҝз„•пјҲStephen KimпјүжһўжңәдәҺ1987е№ҙ7жңҲеңЁйҰ–е°”дё»ж•ҷеә§е Ӯж¬ўиҝҺе’ҢдҝқжҠӨзӨәеЁҒиҖ…пјҢд»–дәҺ2022е№ҙ5 жңҲ11ж—Ҙиў«жҚ•пјҢйҡҸеҗҺиҺ·еҮҶдҝқйҮҠпјҢйҡҸеҗҺиў«зҪҡж¬ҫгҖӮж №жҚ®2020е№ҙ7жңҲ1ж—Ҙиө·е®һж–Ҫзҡ„еҚұе®іиҮӘз”ұзҡ„еӣҪ家е®үе…Ёжі•пјҢд»–д»ҚеңЁжҺҘеҸ—и°ғжҹҘгҖӮ
еӨ©дё»ж•ҷеӣўдҪ“е’ҢйўҶиў–еңЁеҢ…жӢ¬дёңеёқжұ¶еңЁеҶ…зҡ„е…¶д»–еӣҪ家д№ҹеҸ‘жҢҘдәҶеҶіе®ҡжҖ§дҪңз”ЁгҖӮжҲ‘зҡ„жҖқеҝөд№Ӣжғ…зҢ®з»ҷзј…з”ёеһ’еӣәзңҒдё»ж•ҷе·ҙз‘һпјҲCelso Ba ShweпјүпјҢд»–дёҺиҮӘ2021е№ҙ2жңҲ1ж—Ҙиө·еңЁжЈ®жһ—дёӯиәІйҒҝеҶӣдәӢй•ҮеҺӢзҡ„дәәж°‘еҗҢиғһеҗҢеңЁгҖӮ
зј…з”ёжҳҜдёҖдёӘдҪӣж•ҷеӣҪ家пјҢдҪӣж•ҷеғ§дҫЈиҝҮеҺ»жӣҫжҠ—и®®еҶӣдәӢзӢ¬иЈҒз»ҹжІ»гҖӮд»ҠеӨ©еӨ©дё»ж•ҷеҫ’д№ҹеӨ„дәҺеүҚзәҝгҖӮиҝҷйЎ№еӢҮж•ўиЎҢдёәзҡ„е…ёеһӢд»ЈиЎЁжҳҜе®үпјҺзҪ—ж’’пјҲAnn Rose Nu Tawngпјүдҝ®еҘіпјҢеҘ№еңЁзј…з”ёеҢ—йғЁе…Ӣй’ҰйӮҰйҰ–еәңеҜҶж”ҜйӮЈзҡ„е®Әе…өйқўеүҚдёӢи·ӘгҖӮжңҖиҝ‘еҮ еӨ©пјҢжӮІжғЁзҡ„ең°йңҮеҠ еү§дәҶиҜҘеӣҪеҶӣж”ҝеәңеҜ№иҮӘе·ұдәәж°‘еҸ‘еҠЁзҡ„еҸҜжҖ•дё”жҠҘйҒ“дёҚеӨҡзҡ„еҶ…жҲҳпјҢйҖ жҲҗдәҶзҒҫйҡҫжҖ§зҡ„еҗҺжһңгҖӮ
7. еңЁдәҡжҙІи®Іиҝ°иҖ¶зЁЈзҡ„ж•…дәӢ
еҹәзқЈеҫ’е’Ңдј йҒ“иҖ…дёҚиғҪеҒңжӯўйҖҸиҝҮ他们зҡ„з”ҹжҙ»е’ҢиЁҖиҜӯжқҘи§ҒиҜҒиҖ¶зЁЈе’Ңе’Ңе№ізҡ„зҰҸйҹігҖӮзҺ°д»»жһўжңәзҡ„д№”жІ»еҘҘ·й©¬дјҰжҲҲпјҲGiorgio MarengoпјүзҘһзҲ¶еңЁгҖҠеңЁж°ёжҒ’и“қеӨ©д№Ӣең°дҪҺеЈ°е®Јжү¬зҰҸйҹігҖӢдёҖд№Ұдёӯе»әи®®пјҢеңЁдәҡжҙІдј ж’ӯиҖ¶зЁЈеә”иҜҘд»Ҙи°ҰеҚ‘зҡ„ж–№ејҸиҝӣиЎҢпјҢе®һйҷ…дёҠеә”иҜҘдҪҺеЈ°е®Јжү¬пјӣиҝҷ并дёҚжҳҜеҮәдәҺе®ізҫһпјҢиҖҢжҳҜеҮәдәҺеҜ№зҰҸйҹіе’ҢеҜ№иҜқиҖ…гҖҒд»–зҡ„ж—¶д»Је’ҢеҸҷиҝ°ж–№ејҸзҡ„е°ҠйҮҚгҖӮиҝҷдёҺдј ж•ҷзӣёеҸҚгҖӮж №жҚ®й©¬еӨӘзҰҸйҹіпјҢиҖ¶зЁЈеј•з”ЁдәҶд»Ҙиөӣдәҡзҡ„иҜқжқҘжҸҸиҝ°иҮӘе·ұпјҡ“д»–дёҚе‘је–ҠпјҢдёҚеҸ«е–ҠпјҢд№ҹдёҚеңЁиЎ—дёҠеҸ‘еҮәд»–зҡ„еЈ°йҹігҖӮ”
дәҡжҙІзҡ„дј ж•ҷдҪҝе‘Ҫе’Ңж•ҷдјҡдёҖзӣҙз»ҸеҺҶзқҖеҰӮд»Ҡдё–з•Ңи®ёеӨҡең°ж–№жүҖз»ҸеҺҶзҡ„дәӢжғ…пјҡе°‘ж•°дәәзҡ„еӨ„еўғпјҢиҝҷдҪҝд»»дҪ•зү№жқғзҡ„дјӘиЈ…е’ҢжҲҗеҠҹзҡ„е№»жғійғҪиҚЎз„¶ж— еӯҳгҖӮиҝҷз§Қжғ…еҶөеңЁзҰҸйҹід№Ұдёӯ并дёҚйІңи§ҒпјҢиҖ¶зЁЈзҡ„дҝЎжҒҜйҖҸиҝҮз§Қеӯҗзҡ„еҪўеғҸжңүж•Ҳең°иЎЁиҫҫеҮәжқҘпјҢз§ҚеӯҗеңЁйҡҗи”ҪеӨ„з”ҹй•ҝпјҢеңЁз»“еҮәжһңе®һд№ӢеүҚе°ұжӯ»дәҶгҖӮиҝҷе°ұжҳҜзҰҸйҹідј ж’ӯзҡ„ж–№ејҸпјҢеӣ жӯӨдҪҝе‘ҪйҖҸиҝҮзҰҸйҹізҡ„йҖҸжҳҺеәҰиҖҢеӯҳеңЁгҖӮеҹәзқЈеҫ’е’Ңдј ж•ҷеЈ«жҳҜ“жңқеңЈиҖ…е’Ңе®ўдәә”пјҢиҝҷжҳҜж–°зәҰдёӯд»Өдәәеӣһе‘ізҡ„еҪўиұЎпјҢи®©дәәж„ҹеҸ—еҲ°и®ёеӨҡдәҡжҙІеӣҪ家зҡ„еҹәзқЈеҫ’зӨҫеҢәз”ҹжҙ»зҡ„дёҚзЁіе®ҡе’ҢзҫҺдёҪгҖӮ
зҰҸйҹіжҳҜиҖ¶зЁЈзҡ„ж•…дәӢпјҢжҳҜдёҖдёӘеҖјеҫ—иў«иҜҙеҮәжқҘзҡ„ж•…дәӢгҖӮеҰӮд»ҠеңЁдәҡжҙІзҡ„зҰҸйҹідј ж’ӯдёҚеҶҚеҸӘжҳҜдј ж’ӯе®—ж•ҷж•ҷд№үпјҢиҖҢжҳҜи®Іиҝ°дёҖдёӘжңүеҸҜиғҪж”№еҸҳз”ҹе‘Ҫзҡ„ж•…дәӢпјҡиҖ¶зЁЈзҡ„ж•…дәӢгҖӮеҰӮжһңзҰҸйҹід№ҰжҳҜеӣӣдёӘж•…дәӢзҡ„иҜқпјҢйӮЈд№ҲеҸҷдәӢж–ҮеӯҰдҪ“иЈҒжңҖиғҪжҸҸиҝ°иҖ¶зЁЈзҡ„ж•…дәӢе’ҢеҹәзқЈж•ҷзҡ„иө·жәҗпјҢд№ҹжҳҜеңЁдәҡжҙІдј зҰҸйҹізҡ„йҒ“и·ҜгҖӮеҚ°еәҰзҘһеӯҰ家жүҳ马ж–Ҝ·жў…еҚ—её•жӢүе§Ҷзҡ®е°”пјҲThomas Menamparampilпјүдё»ж•ҷеӨҡе№ҙжқҘдёҖзӣҙиҙҹиҙЈдәҡжҙІеӨ©дё»ж•ҷдјҡзҡ„зҰҸдј е·ҘдҪңпјҢд»–ж•ҰдҝғдәҡжҙІзҡ„еҹәзқЈеҫ’е’Ңдј ж•ҷеЈ«и®Іиҝ°“иҖ¶зЁЈзҡ„зңҹе®һйқўзӣ®пјҢжӯЈеҰӮеңЈз»ҸдёӯжүҖе‘ҲзҺ°зҡ„йӮЈж ·гҖӮиҝҷе°ұи¶іеӨҹдәҶ”гҖӮ